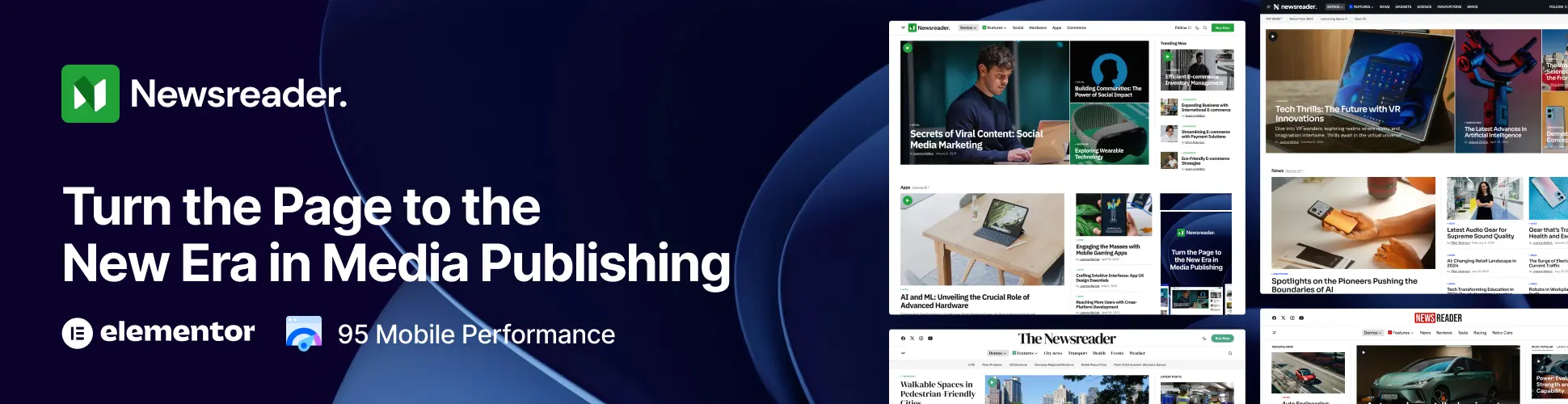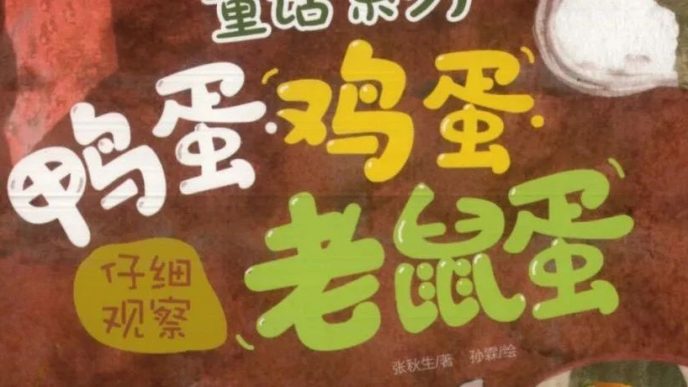30岁这年,我戴上了呼吸机,很可能是终身的,原因是患上了「重度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」。
尽管名称拗口,但它其实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的疾病。公开资料显示,它和高血压、糖尿病一样高发,却远远没有得到同等认知与重视。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患者,直到确诊才迟来地意识到,嗜睡、忘事、精力不济的白天竟来源于每天晚上睡眠时的呼吸不畅。
这种疾病跟生理构造有关,也与生活方式有关。它摧毁了很多人的日常,随着时间积累亦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,中风、猝死、心力衰竭,等等。
可能引发的问题如此之多,许多人还会经历「误诊」:有人因为频繁起夜去看泌尿科,吃下一堆前列腺药物;有人去心内科看高血压,发现怎么吃药也不管用。
对这一疾病,目前成人首选治疗方案是佩戴无创呼吸机,很多患者终身要克服佩戴的不适感,摆脱不被理解的病耻感。据医学期刊《柳叶刀》,我国约有1.76亿睡眠呼吸暂停患者,需要积极治疗的中重度患者超过6000万。然而,国内睡眠呼吸暂停的诊断率不足1%。有医生呼吁,应早日将睡眠科学列为独立临床专科。
无时不在的困
困倦从醒来那一刻就发生了——
程度轻的,在工作开会时打瞌睡;程度更深的,吃着饭就睡着了,碗掉在地上,有位大巴司机被公司催促着就诊,监控发现他开着车几乎要睡着了。1989年出生的陆兵形容这困倦,「完全不想工作,就想赶紧辞职,睡上十几二十天」。
每天上午,这个年轻的销售主管强撑着来到工位,不停做小动作,捏嘴唇,搓耳朵,避免自己直接入睡;挨到午休,也不想着吃饭,他提前就找个没人的房间,一直睡到下午开工。
若不是亲身经历,普通人很难体会到这种「困」带来的伤害。同样作为患者,为了唤醒身体写稿,我不止一次尝试去运动,身体却无法使劲,只能用更简单的办法,洗脸、洗澡、按摩。然而,总是要到晚上,大脑才彻底苏醒,也只持续三四个小时,来不及品尝太久清醒的滋味——
又困了。
放假的日子,经常一连几天,我躺在床上动弹不得,除了吃饭,就在睡觉或者准备睡觉的过程里。这种困,还总是伴随头痛、疲倦,更难受的是,即使成功入睡,也无法进入深度睡眠,总在做梦,醒来甚至更累。
或许正因为工作时间不固定,我体会到的「睡眠碎片化」,比大多数患者还严重,「入睡困难」、「早醒」, 大脑仿佛割裂成两部分,像是没想好到底怎么做,一部分在试图入睡,另一部分却在抵抗入睡。
在这种长期的混沌里,我开始忘记刚认识的访谈对象的名字,借助闹钟来提醒每天的工作事件。许多患者都会出现显著的记忆力衰退,有卖早餐的中年男人不停找错钱;有银行职员走进办公室,就忘了刚刚大厅里还有自己要交办的文件;还有很多人情绪会变坏,变得失去耐心,比如陆兵,他发现自己变得「完全不想和人家说话」。

为了睡个好觉,我尝试过很多办法,不停换枕头、买助眠喷剂、吃褪黑素。四年前,我看了多家医院的精神内科,一份病历记录了当时我的主诉病历:失眠、入睡困难、早醒,诊断为「抑郁状态」、「睡眠障碍」。治疗方案是服用抗抑郁药物——这些药物常见副作用是嗜睡、食欲增加。
我不能断定这些诊断是错误的,至少入睡困难型的失眠有可能独立发生。但现实是,在过去三四年,按时服药的我,伴随着体重增加,睡眠问题依旧日复一日加重。
最近一年,我开始更频繁地夜间惊醒冒汗,气喘吁吁,体会到一些重度患者描述的「被掐住喉咙的窒息感」,有时还伴随着涌上来的酸水(胃食管反流也是睡眠呼吸暂停常见关联疾病)。每天醒来后,喉咙干涩得必须先喝一大杯冰饮才能进食。
这些都是「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」的典型症状。就连失眠,也是这种疾病常见的合并症。有资料表明,22.0%-54.9%的睡眠呼吸暂停患者报告共病失眠,而有29%-67%的失眠患者报告睡眠呼吸暂停。
然而,直到今年5月,在医院做了睡眠监测,我才清晰地看到了问题所在——睡了一晚上,深度睡眠只有30多分钟,不及常人的1/3。平均每分钟,我的气道发生一次阻塞,平均时长18秒,最长的一次,呼吸暂停了54秒之久。最低时,血氧饱和度只有84%,正常人应在95%以上。
普通人每小时睡眠异常事件不超过5次,超过15次即中度阻塞性呼吸暂停,超过30次属 「重度」,而我的数据是68.8次。这还不算多的,有的人发现时异常次数到了170次之多,甚至只能坐着入睡。
拿到这份监测报告,我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情绪:有患病的沉重感,但更多是终于找到答案的轻松感,这种感觉在第二天达到顶峰,佩戴呼吸机的次日,我感觉到了一种久违的持续的清醒,像是被雾霾笼罩多年终于重新看到蓝天。
对于能够佩戴呼吸机的患者来说,感受是类似的,陆兵形容说,「世界特别的亲民」,还有一位常年打羽毛球的患者,发现自己身体反应速度变快了,对方击球过来,大脑还没有反应,球已经稳稳接住了。
治疗效果如此显著,为什么没有早点就诊呢?当我开始试图了解这一疾病的全貌,查阅文献,与更多患者、专业人士交流后,发现事实远比想象中令人震惊,它的患病人群之广,对患者影响至深,但却没有得到该有的重视,乃至被系统性地忽视了。

温水煮青蛙
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(OSA),最常见的阻塞发生于咽部,一个承担着吞咽、发声、呼吸多重功能的部位。然而,往往越精细的部位越容易出现问题。睡眠中,喉部肌肉会松弛下来,对于正常人而言,此时气道虽变得狭窄,但仍算通畅;但对另一部分人而言,通道却因此堵塞。
这种疾病首先是生理性的。研究表明,所有OSA患者都有咽腔狭窄的解剖异常,常见的有小下颌,也就是短下巴。通俗地解释,这类人的气道更狭窄。类似地,肥胖导致的脂肪堆积,也会导致呼吸暂停,就像家具堵塞了过道。
作为一种「异质性疾病」,它在不同人身上会有不同表现,但一个相对容易识别的集中症状是,患者会有不规律的鼾声——呼噜声会突然消失十数秒,那是气道彻底堵塞的结果,直至缺氧触发人体的保护机制,短暂地微觉醒,此时脑电图会出现类似清醒的表现,肌肉牵引力增加,狭窄通道打开,气流重新涌动,再度发出巨大的鼾声。

然而,现实中更多人忽视了这鼾声。或者说,在一个温水煮青蛙般的过程里,很多人逐渐习惯了这种鼾声,就像适应它带来的很多症状。
刚开始,你会经历一段麻木期,浙江的外贸商人黄定军总结说。他是在40岁前后感受到疲倦和乏困的,那段时间,他忙于装修并且帮朋友新开办幼儿园,因此以为是正常的劳累。
然而,体重开始缓慢增长,疲倦感日复一日加重,黄定军原本有跑步的习惯,也变得迈不开腿。每天回到家,灯都不开,他瘫倒在沙发上,刷着短视频。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恶性循环,不仅是肥胖促使呼吸暂停发生,研究也表明,睡眠不足会通过一系列机制加重肥胖。
哪怕只是加班和熬夜,从睡眠医学的角度来说,也可能加重呼吸暂停,此时人体为了自我补偿,会更容易进入深度睡眠。对普通人来说这是休息,对呼吸暂停患者来说,阻塞可能变得更加严重。
再后来,更奇怪的症状在黄定军身上出现了,哪怕没怎么喝水,也没多少尿,他还是频繁起夜上厕所,从一晚上一次,到后来两三次。
他试图找到原因。最初他去看了泌尿科,B超显示前列腺有些肥大,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,这年纪都这样。他买来昂贵的肾宝吃,当然没用,「都是智商税」。在朋友推荐下,他还去了当地精神专科医院的睡眠科,在这里,他的脑袋贴上磁片,诊断出来轻度焦虑。这次配的是镇定药物,也没效果,甚至理论上像喝酒一样,会导致肌肉更加放松,从而加重呼吸暂停。
就这样折腾了两年,直到疫情来临,闷在家里,他开始在网上搜索各种资料,尝试把一切联系起来,包括妻子说的加重的呼噜声、高原反应般的头疼,最终,在医院戴上各种仪器设备做了睡眠监测后,他确认自己其实患上了「中度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」——让他笃定这次找到正确答案的是,戴上呼吸机后,几乎所有症状都消失了。
这样的曲折就诊经历,不是黄定军独有的。十多年前,国内就有多篇论文指出,由于OSA均在睡眠时发病,「常被患者或家属忽略并常以其合并症来就诊,而医生还普遍存在着对其认识不足或不认识或诊断意识不强等问题,因此极易造成误、漏诊。」

一位OSA患者的部分就诊记录,因为醒来乏力疲倦,胸闷、心率高,他连续咨询了许多科室的医生。
「医生有(OSA)这根弦,才会建议病人去做相应的检查和治疗。」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睡眠障碍医学中心副主任黄晶晶说。
客观来说,这种意识一直在提升。在黄晶晶所在的鼾症门诊及专家门诊,大概一半患者是在同寝者的催促下就诊,巨大的鼾声也构成了噪音,而且他们比本人更容易发现睡眠中鼾声的异常乃至「断气」,但也不乏其他科室推荐来的,比如心内科、内分泌科,而且这些年越来越多。
临床上,患者比例视病情程度阶梯式上升,轻度最少,不到1/6,其次是中度,而有一半人像我一样,接受正确诊断时已发展到「重度」。一个典型的OSA患者画像,是身材发福的中年男人,因为长时间的患病脸色暗沉。黄晶晶说,部分原因是,男性肥胖更容易胖脖子和肚子,都影响呼吸。这并不意味着女性能忽视疾病,尤其围绝经期时,可能是激素变化造成上气道解剖结构异常,更易出现OSA。
这是房间里一头真正的大象。黄晶晶说,东亚人的颅面因素更加突出,因此虽肥胖率不及欧美,但OSA发病率接近。最新一份报告里,30岁至69岁人群,我国有超过1.76亿OSA患者,而需要积极治疗的中重度患者有6600万。
但作为同样高发的慢性疾病,OSA引起的重视程度却远远不及高血压和糖尿病。黄晶晶接诊过一位合并高血压的患者,给予了睡眠呼吸机治疗,后来有次随诊,他说自己上飞机时晕倒了,一测是低血压——呼吸机帮助他降低了血压,但他还在服用降压药。
另一个令人悲伤的数据是,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韩芳说,国内OSA的诊断率和治疗率都不足1%。
系统性忽视
每个从事OSA诊疗的医生都在说,这是一种被严重低估乃至轻视的疾病。
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睡眠医学科主治医生周蓉为此提到几个细节:一是疾病名字都没统一,前沿的医疗圈,都用国际规范名称OSA,更简化也更凸显疾病的独立性,但还有很多人在用更拗口的老名字OSAHS;二是在国外,治疗OSA的仪器叫CPAP(持续气道正压),重症监护室用的则叫NIV(无创通气),但在国内两者都叫无创呼吸机,可能会让患者误解,从而更抵触治疗。
还有其他专业人士提到的一些细节,则更凸显了系统性的「忽视」。比如在一些发达国家,用于治疗OSA的CPAP呼吸机由医保支付,但国内需要自己购买。又比如在一些地区,针对体重严重超标者,发放驾照前必须通过睡眠监测,而在国内目前没有相应的机制。
就连睡眠医学本身,或许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。这门科学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伴随睡眠监测技术发展,在美国率先建立起来的,或许是发展时间短,即使在国外它也算小众学科。
在国内,它还要小众得多。在美国、欧洲等发达国家,睡眠医学已经是独立学科,有独立的人才培养体制,但在国内,学位教育部门前不久才将之作为三级学科,纳入内科学研究生学位培养体系。
国内睡眠医学带头人韩芳说,当务之急是将睡眠医学列为临床上的专科。据他说,仅OSA一项疾病,以目前的诊疗速度,全国的存量病人约在300年后才能诊断完。

现实中,一个很可能会让患者困惑的事实是,在不同医院,睡眠监测病房是属于不同科室的,有设在耳鼻喉科的,有呼吸科的,有精神科的,还有口腔科的。从事OSA诊断的医生们,执业证书上都不是睡眠医学,而是内科学、精神卫生学、耳鼻咽喉科学等。
这些年,人们越来越意识到,这是一种需要多学科合作的疾病。北京大学第六医院,这家国内排名第一的精神专科医院,它的睡眠医学科在四年前引入了像周蓉这样的呼吸内科医生。
周蓉说,对精神科医生来说,呼吸机不是专业培训的内容,而睡眠呼吸暂停的首选治疗手段就是呼吸机,指导患者呼吸机的使用就是她在科室内承担的工作之一,尽管医院本身并不出售呼吸机。
她还单独开了一个鼾症门诊,一周五个半天——但多少显得门庭冷落,甚至一半的人,来了都不是看病,只是别的大夫挂不上,挂到她这儿开药。
在她看来,一个更理想的睡眠医学科室,除了精神科、呼吸科医生,还可以再引入耳鼻喉科、口腔颌面外科医生,最理想的再联合内分泌营养、心血管医生,但这不太现实。
不过,对最需要及时治疗的中重度患者而言,呼吸机已经是首选——通过外加的气流吹出一条通道,保证了患者睡眠时呼吸的通畅。更完整的治疗指南,也包括减肥等一般性治疗,戒烟戒酒慎用镇静类药物等,因为有风险且易复发等原因,外科手术多用于不能耐受呼吸机的情况。
或许,一个更简单但有用的判断依据是,观察世界范围内最有权势和财富的人在采用何种治疗方式:拜登经常被发现脸上出现佩戴呼吸机的勒痕,他的发言人说美国总统用呼吸机在治疗OSA;在国内,名流霍启刚、奥运冠军杨威、明星王栎鑫等人,也都采用呼吸机治疗,明星胡海泉还曾在节目中演示如何佩戴呼吸机,主持人汪涵当时形容,「像睡在重症监护室里一样」。
也有例外,台湾明星陈乔恩就做了手术,因为鼻子过敏,她无法佩戴呼吸机,而是开刀,「把喉咙扁桃腺切掉、把睡眠时会塌陷的地方的肉拿掉」。
这位女星去年发长文分享了这段经历,在人生的前40多年,她都没意识到自己患有这种疾病,直到丈夫艾伦被她「恐龙般」的鼾声吓住,伸手探她的鼻息,「发现真的停了很久」。

拒绝看病的人
如今回看,故障信号灯其实一直在闪烁。
最近几年回老家,我总被母亲提醒,鼾声变得更加巨大,甚至超过了父亲。两年前的夏天,一次在办公室,下午三点我睡着了,巨大的鼾声还遭到过附近同事的投诉。
然而,我只以为是变胖的缘故。去减肥吧,家人和朋友很多次给出建议。我也不止一次努力过,却始终无法坚持,甚至后来再被劝时变得焦躁,觉得不被理解,你怎么能要求一辆发动机出状况的汽车去跑高速呢?
事实上,接受正确治疗两个月后,我才重新拥有每天运动的能力。尽管有研究表明,减肥后,大部分轻症患者疾病缓解,但我这样的重度患者,只有13%会得到缓解。
两年前,我还得到过更针对性的提醒。那次,我和朋友吃饭,他确诊了睡眠呼吸暂停,提醒我也可以去医院做睡眠监测。当时他就关注到我下巴显短,还提到呼吸机,我睁大眼睛表达了惊讶,仿佛听闻了多么可怕的事。

或许病耻感的根源正是无知和偏见。哪怕黄定军这样,愿意向我细细复盘病历的患者,也只在小圈子分享经历,碰到那些认为「睡个好觉是天经地义」的朋友,他会选择闭嘴,「对我们睡眠障碍的人来说,睡个好觉真是一个需要去奋斗的事情。」
但哪怕劝说最亲近的人去就医,也相当困难。这几个月,我好多次提醒同样打鼾严重的父亲去做睡眠监测,他回答「再看看」,而母亲听到可能要终身佩戴呼吸机显得无法接受,「这还得了」。朋友也遇上了一样的苦恼,甚至为了这事和他父亲吵了起来。
理论上,年纪越大,肌肉的控制力下降,越容易患上OSA。然而,宁波一位呼吸机经销商统计过,85%的睡眠呼吸机购买者是青壮年。尽管多数情况下OSA并不致死,但作为一种「上游疾病」,在日复一日的缺氧、睡眠中断下,它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等疾病,而许多人直至死于并发症,都没意识到患有这种疾病。
临床上,周蓉也见了太多抗拒治疗的患者,并且从综合医院来到精神专科医院后,碰到更多心理上不愿用呼吸机的患者,从心理学专业描述,可能是因为「灾难化思维」和对负面因素的「选择性注意」。她则会拿眼镜、人工耳蜗作为比较,告诉对方,「这是现代科技带给我们的福利」。
或许还有更深层的心理原因。周蓉也是人到中年体会到这点,这两年她胆固醇偏高,却发现自己抗拒吃药,不愿意听从医生建议,为什么会这样呢?她想到一个答案,当我们在抵触治疗的时候,「可能是在抵触衰老、抵触生病,抵触自己越来越走下坡路」。
(文中陆兵、黄定军为化名)
【参考资料】
1.徐培成等.《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,肥胖,代谢综合征的病理生理联系及治疗进展》检验医学与临床 21.8(2024):1176-1181.
2.房凤凤等.《合并病态失眠和睡眠呼吸暂停的研究进展》中华保健医学杂志 25.3(2023):365-368.
3.黄东海.《浅谈成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临床诊疗中的困惑》中国耳鼻咽喉颅底外科杂志 28.5(2022):1-5.
4.何权瀛, and 王莞尔.《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诊治指南(基层版)》中华全科医师杂志 7(2015):7.
5.李哲等.《中国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病人的人口学特征》第四届中国睡眠医学论坛论文汇编 2011.
6.黄筱文.《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临床研究现状综述》医学综述 12.012(2006):750-752.
7.黄席珍.《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历史现状和未来》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6.5(2003):2.
本文转载自【极昼工作室】
关注查看更多故事


亲爱的读者们,不星标《人物》公众号,不仅会收不到我们的最新推送,还会看不到我们精心挑选的封面大图!星标《人物》,不错过每一个精彩故事。希望我们像以前一样,日日相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