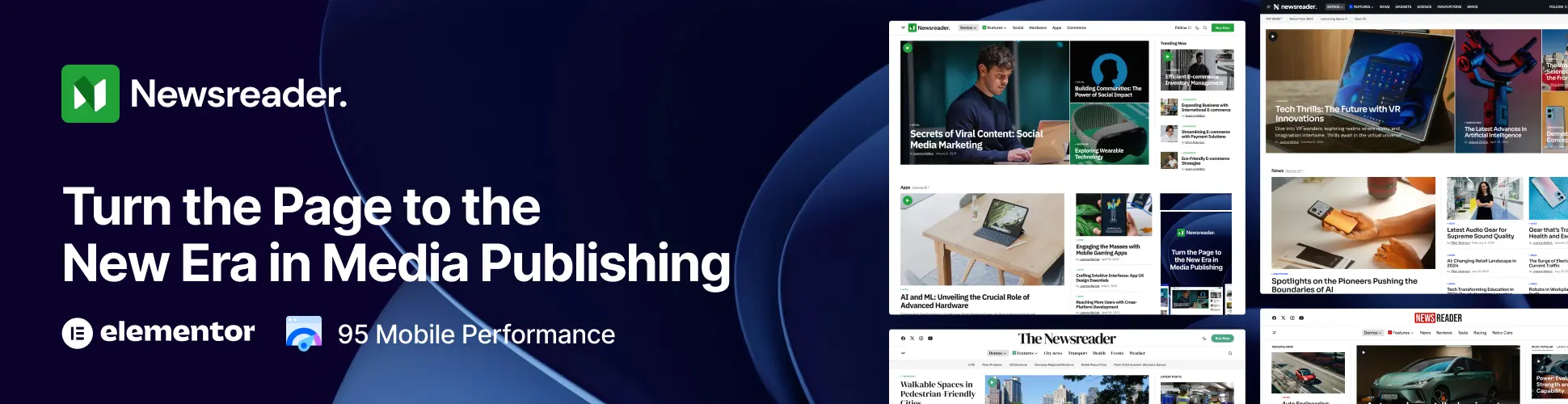“
过去4年,深漂女诗人邬霞在单身妈妈和打工作家的身份里进退失据。
28年前,14岁的邬霞从四川故乡初中辍学,到深圳成为一名女工。2014年,她作为工人诗歌电影《我的诗篇》中唯一一位女工诗人,走进大众视野。
今年,邬霞42岁。作为单身母亲,她和两个女儿居住在城中村。尝过学历低下、经济贫困的苦,她如今苦苦追逐着超大城市水涨船高的准入门槛,努力阻止两个女儿陷入和她类似的命运。
 “颗粒无收”的上半年
“颗粒无收”的上半年
夏夜,深圳西乡共乐旧村一栋抱手楼内,邬霞躺在客厅的旧沙发上,面色苍白忧郁。
屋内,斑驳的墙壁上粘着一张墨绿色海报,是她在自传《我的吊带裙》新书分享会时留下的,邬霞母亲捡来准备去卖的纸壳,占据了院子里一小块空地。这是邬霞在城中村住了3年的家。
今年,邬霞42岁了。自14岁初中辍学,她随父母深漂28年,一直租住在深圳市宝安区“相依为命”。邬霞另外的身份是作家,也是一位单亲妈妈。她19岁开始在打工文学刊物上发表短文,2015年,成为工人诗歌电影《我的诗篇》中出现的唯一一位女诗人,走上上海国际电影节红毯,后来又登上央视,这是她人生的高光时刻。此后这10年,邬霞不断和贫困斗争,离婚、父亲重病、贫困……也时常出现在媒体上。而她的困顿,也常常成为她被攻击的理由。
6月底,邬霞在出租屋的厕所门前跌倒。她感到水泥台阶坚硬锋利的边缘直抵背部,背部很快肿痛起来。看病要钱,她在出租屋里硬挺了2天,拍了受伤处的照片发给附近一个开推拿店的小老板看,对方判断说是“骨裂”。这种情况难以自愈,于是,伤后第3天,邬霞才由母亲用轮椅推着,穿过不平的小巷,抵达宝安医院。在医院经过一番检查,医生诊断邬霞2-4根腰椎,横突骨折。从医院回到家,邬霞按照医生的嘱咐服药,在家休养。她每天起床后只能斜躺在客厅的旧沙发上,忍受着背部“发神经似的疼痛”。
用邬霞自己的话说,2024年上半年,她忙碌,但“颗粒无收”。
2月末,因父亲患带状疱疹住院,邬霞和母亲、妹妹轮流在医院陪护。邬霞负责一整个白天。清早,她六点半送两个女儿上公交车,就赶去医院,给父亲擦药、换尿垫、喂饭,紧盯着他的需求。陪床27天,父亲睡着的间隙,她抱着手机刷题,准备5月份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的考试。
回家后,她接着用电脑上课、刷题。为赶进度,常常要熬夜到凌晨两三点。
3月底,一家省级刊物向邬霞约稿,1万字左右的约稿,她写了一个月。忙起来的时候,她就利用碎片时间,在手机上写几行字,回家再复制到电脑上。这笔5千余元的稿费8月发放,因此上半年还是颗粒无收。
因为经济困顿,家人们其实希望,邬霞这次骨折伤好后,能够去找一份工作。
另一方面,在家养伤的邬霞,为一件和钱有关的事焦灼不已——两个女儿读私立学校统共需要一万六千余元的学费,尚未凑齐。
受伤前一周,邬霞刚刚为大女儿申请了初中学位。深圳实行积分户籍制。作为外地户籍人员,邬霞只有拥有对应学历,再加足够的社保年限,攒够积分落户,孩子才能读公立学校。
14岁,她到深圳打工,35岁才在深圳交上社保。为了入户给孩子办入学,2020年起,她在照顾孩子、写作之余,也开始学习,准备自考大专及工程师。去年,她靠自学拿到大专毕业证书。
6年的社保,加上自考的大专文凭,邬霞几乎榨干了自己这些年空闲的时间,终于在手里攥了67.6分。不过,距离孩子入学公立学校74分的门槛,还差6.4分,她依然只能给大女儿申请私立初中的学位。
在公众号上,她记录了这些年漂泊于深圳无房、无户口的困窘与无助,却招来谩骂。有人将她与同因《我的诗篇》走入民众视野的诗人陈年喜比较。说她天分与才华耗尽,“继续写作也是浪费时间”。有人因她生存维艰还“做文学梦”而不满,说要骂醒她。
邬霞在留言下回复,讲述她作为单身妈妈,凭一己之力要解决孩子的户籍、房子和生活费的不易,对方却讽刺她作为清贫的诗人对房子和户口的渴望:“你要等到一间大房子才来写作吗?”
在贫穷的催磨中,记录和写作作为宣泄,一直是邬霞少有的精神出口。2022年,邬霞的自传体书籍《我的吊带裙》出版,她在书中袒露了打工往事与一段婚姻,却因一些细节不符合读者对“完全解放的女作家”的期待,而招致攻击。名气为她带来的,更多是凝视,她曾在采访中讲述了妈妈为一家人付房租的故事,又招来了“啃老”的骂名。
这些注视难说是否过于苛刻。拥有共同来处的邬霞和陈年喜,仍在线上保持着联系。2022年9月,邬霞出新书后,陈年喜在朋友圈为邬霞发言,说出她作为出书背后,作为贫困的单亲妈妈,不易的处境:“她没有如我们这些男性广泛阅读的时间、自由和条件,也少有广阔涉及社会生活层面的机会,思考、写作到这个层面已堪称优秀”。
 图 | 邬霞在家中
图 | 邬霞在家中
 坠入贫困之中
坠入贫困之中
 图 | 2月末,邬霞在医院陪护父亲
图 | 2月末,邬霞在医院陪护父亲 拖拽
拖拽在《东京贫困女子》一书中,记者出身的作者中村淳彦曾总结过对女性陷入贫困的原因的观察:贫困,是在出身和成长经历、家庭环境、健康状态、就业、政策、制度、个人和配偶的性格及人格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的。每个人面对的现实五花八门,各不相同。
邬霞21岁时被催婚。她从身边的女孩身上见过婚姻的模样。发小结婚后,和丈夫住在铁皮房内。妹妹生完孩子4个月后,孩子被婆婆带回老家,妹妹做不了主,只能暗自哭泣。
“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未来?”邬霞一度抱着不结婚、靠写作养活自己的想法。微弱的女性独立意识萌芽,现实生活却并未给它提供野蛮生长的土壤和养分。
2009年,邬霞和父母相继失业。作为家中长女,邬霞把父母养老的责任背负在身上。她意识到,靠自己想要在深圳立足,并不现实。
邬霞在写作中展示出的大胆热情和生命力,和她在婚恋上的退守传统相当矛盾。这在她的成长轨迹中又有迹可循。
在工厂时,阅读言情小说是邬霞的精神出口,以至于工厂区充斥规训和异化的生活,没有阻挡邬霞飞扬的想象力。但阅读言情小说也强化着女性需要被男性看见、对男性依附的暗示。
正如学者珍妮斯•A. 拉德威在《阅读浪漫小说》一书中所分析,浪漫小说塑造了百分百关注和迎合女性需求的男性,同时也强化了属于女性的情感陷阱,女性只需纯真、善良、美丽,自然会获得男性的关注与支持。
潜移默化地,邬霞希冀着在婚姻中追求“浪漫爱”。
也是在那前后,邬霞经人介绍认识了前夫。前夫和她一样来自农村,认识时,告诉她自己“年入十几万”。邬霞坦承,那是她已对流离失所的生活深恶痛绝,想要退回看似安全的传统婚姻和家庭中。她梦想着,婚后“男主外,女主内”,她一面相夫教子一面继续写作,两人能齐心协力地建设小家庭,以后在深圳安居乐业。
谈恋爱时,男人以借工程款的名义,陆续借走她的存款,她想着“都是一家人”,没有防范。听到他和别人吹嘘“输光了”工程款,她才发现他口中的“打点小麻将”其实是赌博。2011年,邬霞生下大女儿,前两年,女儿需要24小时照顾的时候,邬霞抽空写文章勉强为生,一度要靠父母接济。2013年怀第二个孩子时,男人说:“如果是女孩子。你自己养。”
二女儿出生后,她独自照顾两个女儿,有时在电脑上刚打上两行字,女儿就哭闹着找妈妈,她才意识到,独自照顾两个孩子几乎不可能同时兼顾写作。
2017年,邬霞离婚时只得到了小女儿的抚养权。当前夫将大女儿送回她身边,要她带着读书时,邬霞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。有人劝她,多为自己想想,把大女儿交给奶奶带。但邬霞做不到。离婚前一年,邬霞去湖北探望大女儿,当时孩子跟着爷爷奶奶在老家读书,她看见的,是孩子张开双手要妈妈抱,站在堆着衣服的床边写作业,脸色蜡黄。还有一次,大女儿坐在爷爷的三轮车上翻车,“腿上缝了七八针”。
离婚那年邬霞34岁,和社会脱轨4、5年。得到了一位文友的提醒,她才知道,女儿们想要在深圳读书,需要先拿到深圳户口。文友帮她梳理了自考大专和工程师的流程,她开始备考。
也因花钱自考,她又往贫穷的深处更进一步。
2018年,两个女儿进入小学,邬霞每天清早6点起床,往返3小时接送两个女儿。在家时,她要去买菜、洗衣、打扫、给在家养病的父亲做饭。看书和考题,占据了她本就不多的阅读和写作时间。
去年,邬霞靠分期付款维持开支,自考拿到大专文凭,这给了她很大的信心。2020年前后,她开始准备工程师考试,这项自考一年有2次,分别在5月、11月。每年考试月提前两三个月,邬霞每天还要花上几个小时听直播课、刷题。考试对她来说难度不小,她去年考过一次,没过,今年上半年的考试宣布取消后,只剩下一次机会的邬霞更觉压力。
6月骨折之后,邬霞在家中休养了近两个月。听课、写作都需要使用电脑,无法坐下,意味着她长时间无法写作,两个月没有收入。
赶在8月30日学校划学费前,邬霞从网贷上借了一笔钱周转。之后,她收到了《天涯》杂志的稿费,得以偿还部分借款。
生活似是永恒这般捉襟见肘。解决了学费的危机,邬霞父亲的身体,有了新的病兆。他的牙齿一颗颗脱落,吃不下什么。虚弱到站起时双腿颤抖,连行走时也需要家人牵着前行。
邬霞考虑着,该去再次找一份工作了。她计划投一些文案类的工作,不管怎样,先试一试。
28年来,邬霞回过故乡两次。家里的房子已经坍塌,住在县城的亲人也多已离散。故乡对于42岁的她来说,是年幼时曾居住过14年、再也回不去的地方。
多年后她见到读书时的同桌,对方说起当初邬霞辍学下深圳打工的事:“我觉得你好酷。我也想这样!” 邬霞不附和,反而和他开玩笑,“你当时怎么不拦我一下?”
内心深处,邬霞真的希望当时有人能拦住辍学的自己。她记得父亲当时说 “女孩不用读太多书,会写信就行”,远在深圳打工的母亲听后,哭了整整一夜。如果那时候有人拦她一下,就好了——邬霞想——把书继续读下去,人生或许能因此多出更多选择。 因此,在为女儿选学校的时候,她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申请了质量相对最好、学费最贵的那一个。
过去一年,邬霞统计过,她靠稿酬、奖金、文友介绍的劳务工作,平均月收入大约有5千多元。去掉她的社保、孩子的学费,她还坚持供着给自己和女儿买的商业保险。那本是邬霞在妹妹做保险销售时为帮衬妹妹买的,保费一年要万余元。后来经历愈多,她越发坚持续保。
原因无它,邬霞想给自己和女儿购入一份保障,不用像2013年那样,父亲突然病重,没有医疗和商业保险报销,一家人倾尽积蓄还负债。
最近,邬霞发现大女儿的性格愈发沉默。前段时间,开朗的小女儿也说“不想读书”,学校太远了。积分不足的邬霞没有太多择校权,两个女儿就读的是隔壁村的民办学校,通勤要转公交车加走路,一度早上去学校要50分钟。她们清早6点半要起床,在家来不及吃饭时,就拿着包子混合着汽车尾气将早餐吃进去。
她问女儿,不读书你想要做什么?小女儿说:“想躺平”。邬霞因为这个答案很紧张,也内心酸涩。她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拿到工程师的证件,这赶得上能让小女儿读教学质量更好的公立初中。
她依旧不知道,自己能支撑孩子读书多久,两个孩子的学费要从哪里来。只是,贫困又无能为力的日子她过够了,她决心尽己所能拖拽,让两个女儿免于循环她的一生。
往期回顾